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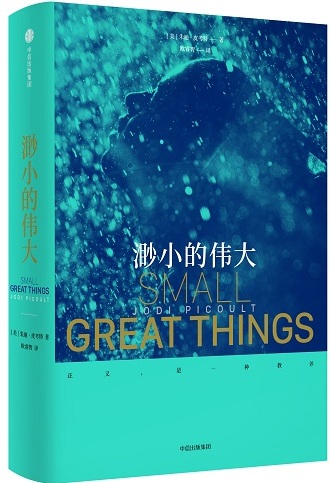
[书籍信息]
书名:渺小的伟大
作者:[美] 朱迪·皮考特
译者 欧睿智
定价:49.80
出版日期:2018-6-1
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
书号ISBN 978-7-5086-8696-7
[作者简介]
朱迪·皮考特,美国当代畅销书作家、小说家。自1992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以来,其十五部作品无一不持续畅销,包括《离别时刻》《说故事的人》《姐姐的守护者》《换心》《小心轻放的爱》《19分钟的眼泪》等。每有新作,即迅速登上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亚马逊网站等畅销书榜。
她常常将小说中的人物置于道德困境之下。面对挑战,真实的人性弱点暴露无遗。这也使得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话题性,引起广泛争议和探讨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作家并非只是抛出问题,而是运用难以置信的共情、智慧和剖白坦率的心理描写,对自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反思,榨出芸芸众生华贵皮袍下面那些有瑕疵的灵魂。同时,她也给予我们每个平凡之辈以信心和勇气,只要坚持一点点的正义,这个世界就有被改变的可能。
[内容提要]
“这世上很多的罪恶,都来源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。”
从小,鲁斯就知道,她和别人不一样。她的皮肤是黑色的,妈妈给白人家庭做保姆,供养姐妹俩读书。鲁斯发奋努力考入医学院,成为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护士。一天,在她给新生儿进行例行检查时,却被上司告知,严禁接触这个婴儿。原来,婴儿的父母信奉白人至上,强烈要求鲁斯(非裔美国人) 远离他们的孩子。
第二天,鲁斯到医院加班,在手术休息室里,她发现昨天护理的那个婴儿突然出现呼吸困难。护士的本能驱使她立刻准备予以急救,但一秒钟之后她犹豫了,她想到了那道禁令,同时阻止她的,还有她内心长久以来对偏见与歧视的愤恨。她没想到的是,更可怕的命运,正躲在背后虎视眈眈……
[编辑推荐]
如果你是护士,面对一个突然出现呼吸障碍的婴儿,本能驱使你立刻施救,但你的上司刚刚传达了一道禁令,婴儿的父母严禁你触碰这个婴儿。那么此时,你救还是不救?
如果你现在被指控谋杀,你的辩护律师一路披荆斩棘,胜算十足地进入总结陈词阶段,你只需保持沉默即可被无罪释放,那么此刻,你会冒着满盘皆输的风险,说出所有真相吗?对得起良心的真相?
这是畅销书作家朱迪•皮考特的震撼力作,和她那本风靡全国的小说《姐姐的守护者》一样,新作《渺小的伟大》依旧充满道德争议与灵魂拷问,令人心痛得几乎窒息。朱迪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,而是通过描述医生、护士、律师、法官等每个人物的复杂心理,毫不留情地榨出我们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。
这本书被誉为21世纪的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,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杰作。同名电影由朱莉娅·罗伯茨、维奥拉·戴维斯主演 ,斯皮尔伯格影业年度巨献。
本书书名取自马丁·路德·金的语录:If I cannot do great things, I can do small things in a great way(我也许不能成就伟业,但我能以伟大的方式做好小事)。希望这本书能给予我们每个平凡之辈以信心和勇气,只要坚持一点点的正义,这个世界就有被改变的可能。
[书摘]
紧急剖腹产的可怕程度世间罕有。只要医生做出要紧急剖腹产的决定,气氛就开始高度紧张, 对话都变得简明扼要: 我已经进行静脉注射了; 你能把床推过来吗? 来个人把药箱拿过来, 再把这件事记下来。还要告诉病人现在出了点问题, 我们需要快速移走。你和护士长忙着把病人推到产房的同时, 医院领导会通知到每一个现在不在楼里的团队成员。护士长把包装纸撕开, 拽出里面消过毒的器具, 打开麻醉设备。与此同时你负责把产妇扶到产床上, 把她的腹部露出来, 把围挡布帘拉好。医生和麻醉师冲进门来, 切开腹部, 取出婴儿。整个过程不到20 分钟。而在耶鲁- 纽黑文这种更大的医院, 他们甚至能在7 分钟内完成紧急剖腹产。
德维斯·鲍尔的微型包皮环割手术结束20 分钟后, 科琳娜负责的另一个病人羊水破裂了, 缠绕着的脐带从她的两腿之间流了出来。科琳娜被从新生儿室紧急叫走去处理这件事。她边冲向那个产妇的病房边冲我喊: “帮我盯着这个孩子!”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玛丽走到这个病人的床头, 拉着她向电梯走去。科琳娜跪在病人的双腿之间, 她戴着手套的双手在阴影处忙活, 试图把脐带塞回去。
帮我盯着这个孩子。她的意思是希望我来照看德维斯·鲍尔。按照规矩,在这个手术完成后应该对婴儿定时检查, 防止他流血。而现在玛丽和科琳娜忙着照顾那个紧急剖腹产的病人, 所以理论上已经没有人手来盯着这个婴儿了。
我走进了新生儿室, 德维斯·鲍尔从早上手术之后一直在昏睡。我劝慰自己, 科琳娜回来之前我只需要看他20 分钟, 说不定在此之前玛丽就先回来解救我了呢。
我紧抱双臂, 低头盯着他。新生儿不过是一张白纸,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他们父母的观点, 或是宗教的习俗, 或是把人按照自己的好恶划分。准确地说,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想法都没有, 可能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被照顾。他们不加评判地吸收别人传达的内容。
我在想后天的教育在多长时间之内会腐蚀掉那种天生的纯净。
等到我再次低头向婴儿车里看去时, 德维斯·鲍尔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我弯腰靠得更近了一些, 才确认原来是我没有看清他胸部微小的起伏。但是从我这个角度看, 他的肤色开始泛青了。
我立刻伸手, 把听诊器贴在他的心脏上, 拍打他的脚后跟, 解开了包裹他的毯子。很多婴儿都会在睡觉过程中窒息, 但如果把他们稍微挪动一下,把他们从平躺翻成趴着或者侧躺, 他们就会自动恢复呼吸了。
我的手突然顿住了。那句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: 不能派非裔美国人照顾这个病人。
我急忙回头向新生儿室的大门看去。以我现在的姿势, 如果有人进来,他们也只能看到我的背影, 而看不到我具体在做什么。
他们会认为我给他刺激实际是在救助他, 我碰他是一种关爱的体现吗?
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举动而解雇我?
我是在为了区区小事斤斤计较吗?
如果这个婴儿恢复了呼吸, 是不是就没事了?
这些想法在我脑海中激荡盘旋: 这一定是呼吸骤停; 因为新生儿从来不会出现心脏问题。一个婴儿停止呼吸的时间可能达到三到四分钟, 但是心跳还能保持在100。这是因为正常的心跳是150……这说明就算血液无法抵达大脑, 但仍然会流到身体的其他各个部分, 只要能让婴儿吸氧, 心跳很快就会恢复。因此一般都不会选择给婴儿进行胸部按压, 而是直接给他们输氧。而对于成年病人, 处理方式正好是相反的。
现在我试图把这些疑虑赶出脑海。我尝试了每一种在手边缺少药品和设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方式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, 我会拿一个脉搏探测器,测量一下他的吸氧量和心跳速度。或者是拿一个吸氧面罩。再或者, 叫人。
我究竟应该怎么做?
我究竟不应该做什么?
科琳娜和玛丽随时都可能走进新生儿室。她们会看到我介入了这个婴儿的事,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?
我手忙脚乱地重新把婴儿用毯子包起来, 汗水顺着我的后背流了下来。
我盯着这个小小的婴儿, 我的耳鼓因心跳过快而剧烈地震动着。我失败了。
我不知道是过去了3 分钟, 还是只有30 秒。玛丽的声音突然从我背后响起: “鲁斯, 你在做什么呢?”
我虚脱地说: “我什么都没有做。”
她越过我的肩膀看向婴儿, 发现他的脸颊已经泛上青色。她立刻看向我的眼睛, 给我下命令: “去拿我的急救包。” 她边说边解开婴儿的毯子, 拍了拍他的小脚, 并帮他翻身。
和我刚才采取的对策一模一样。
玛丽把婴儿用面罩罩在德维斯的口鼻上, 开始按压气囊, 向他的肺里充气。她说: “你去拨……”
我根据她的指示拨打了1500。我对着广播说: “新生儿室出现紧急情况。” 我想象着大家都抛下了手头的工作向这里赶来: 麻醉师、重症监护护士、记录护士, 以及从另一个楼层赶来的护士助理。还有儿科的阿特金斯医生, 几分钟前她才离开这个婴儿身边。
玛丽对我说: “开始按压。”
这一次我没有犹豫。我用两个手指向下按压婴儿的胸部, 每分钟按压200 次。当急救车被推进新生儿室时, 我伸出空着的那只手拽过导线, 把电极贴到婴儿的身上,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心跳监控器看看我的按压是否奏效了。这间狭小的新生儿室里突然挤满了人。这个身长不到50 厘米的小病人周围人头攒动。麻醉师对正在寻找头皮静脉的重症监护护士大叫道: “我试一下把管子从这里插进去。”
护士喊着: “我没有肘部穿刺①的导管。”
麻醉师说: “我来了。” 然后他向后退了一步, 让护士可以更靠近地操作。护士把针刺了进去, 我又加重了按压的力度, 希望这样至少能有一条静脉明显地突起。
麻醉师盯着显示屏, 对我大声说: “不要按了。” 我抬起手, 感觉就像在犯罪中途被人抓了个现行。
我们都看着屏幕, 但是婴儿的心跳只有80。
麻醉师说: “按压的作用还不明显。” 所以我继续更加使劲地按起了胸腔。他的胸腔线条是那么漂亮。现在他的肚子上还没有长出肌肉, 来保护那个小小肚皮里的各个器官。
如果我的手指太过向下, 或者远离了中心部分, 我甚至可能会把婴儿的肝脏按碎。
玛丽说: “这个婴儿的脸色还没有恢复红润。氧气还在加吗?”
麻醉师说: “谁能去拿一下血气仪?”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回荡在婴儿的上空。
那个重症监护护士把手伸到婴儿的腹股沟测试脉搏, 从婴儿大腿动脉上抽了一点血样, 检查一下他有没有酸中毒。急救小分队的另一个人立刻拿着血样向实验室冲去。但是等到我们拿到检测结果时,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因为等到那时, 这个婴儿要么已经恢复了呼吸, 要么永远地停止了呼吸。
“可恶, 为什么现在还没拿到导管?”
重症监护护士说: “你想试试? 请便吧。”
麻醉师又命令道: “停止按压。” 我停了下来。此时显示屏上显示心跳为90。
“给我阿托品。” 有人给医生递过去一个注射器。他拔掉了针头上的盖子, 挪开充气气囊, 把液体注射到婴儿体内, 让它流到肺里。然后他继续按压气囊, 让氧气和阿托品进入婴儿的细支气管。
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要分秒必争, 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难挨, 到最后你都说不出来自己是正在经历这一刻, 还是在想象中完成每个动作。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正在飞速忙碌, 仿佛这双手根本不受你自己支配。你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渐渐增强, 升级成骚乱, 最后汇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刺耳音调。
重症监护护士提议: “要不我们给他的肚脐插管吧?”
玛丽否定了: “不行, 他现在出生的时间太久了。”
情况很快急转直下。出于本能, 我按压的力道更大了。
麻醉师说: “你按得太使劲了, 轻一点儿。”
此时一声尖叫打断了我按压的节奏, 布列塔妮·鲍尔走进了这个房间, 然后开始哀号。她挣扎着想冲到婴儿身旁, 负责记录的护士拉住了她。她的丈夫则错愕地站在原地, 一动不动, 盯着我在他儿子胸口按压的手指。
布列塔妮哭着喊道: “他怎么了?”
我不知道是谁让他们进来的,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下根本没人有精力顾得上把他们挡在门外。从昨天晚上开始, 妇产科就一直超负荷运转, 而且人手不足。直到现在科琳娜还在产房里处理那个紧急剖腹产的产妇, 而玛丽和我一起在这里抢救这个婴儿。鲍尔夫妇可能是听到了刚才的紧急广播, 或是看到医护人员冲向新生儿室。而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接受完微型包皮环割术后, 本来应该在这个房间里安静地沉睡。
换作是我, 我也会立刻奔来的。
房门被一把推开, 儿科的阿特金斯医生推开众人径直走到婴儿车的床头, 问: 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
没有人回答。此时我才意识到应该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。
我说话的节奏仍然和手中的按压频率一致: “当时我和这个婴儿在这个房间里。他的脸上渐渐没了血色, 呼吸也停止了。我们给了他刺激, 但是他并没有吸入空气, 也没有自主呼吸, 所以我们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。”
阿特金斯医生问: “你按压多久了?”
“15 分钟。”
“好吧, 鲁斯, 现在你可以停一……” 阿特金斯医生看向显示屏上的数字。心跳现在掉到了40。
玛丽轻声说: “墓碑。”
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。每次心电图上QRS 波群的宽度过宽时, 我们都会说这个词。因为这种波形表示右心室对左心室的反应过慢, 所以没有心跳输出。
已经没有希望了。
几秒钟之后, 他的心跳彻底停止了。阿特金斯医生说: “我来宣布……”
做这种事的过程总是很艰难的, 更何况还是一个新生儿。她深吸了一口气,把气囊从呼吸管上拽下来扔进了垃圾桶里。“现在的时间?”
我们都抬头看向时钟。
布列塔妮一下子跪到地上, 哭喊着: “不! 你们不要停下来, 不要放弃。”
儿科医生说: “鲍尔太太, 我们深表遗憾。但是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, 他已经去世了。”
特克挣扎着从他妻子身旁冲过来, 从垃圾桶里掏出气囊。他一把推开麻醉师, 试图把这个东西重新装到德维斯的呼吸管上。他祈求我们: “快教教我怎么用, 我来负责按, 你们不要停下来。”
“请你……”
“我可以让他恢复呼吸的。我肯定可以做到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