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,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的问题何以产生,而中国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识、经济和情感解决它们。
——史景迁(Jonathan Spence)
研究腐败高发期从古代中国说起,既有历史的依据,也有逻辑的必要。诚如黑格尔所言:“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,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,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。它的原则又具有一种实体性,所以它既是最古的、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。……‘实体的东西’以道德的身份出现,因此,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,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。”
1.传统之“型”:断头政治下的山寨式腐败
17世纪,被西方史学家称为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”和“中华帝国的开放年份”。在此之前,“4000多年中,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、自治的社会。这一社会……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,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。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、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、从属的社会”。此后,曾雄强于欧洲的中国,发展开始减退,国力开始衰弱,国门开始闭锁。而随着西方世界开始兴起,旧中国的统治者将要在农业和工业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中甘拜下风。
与现代社会人们所能接触、知晓的腐败不同的是,17世纪晚明的传统“中式”腐败是发生在无视乃至没有公民权利的专制政体背景下。总体上看,传统腐败是以财产侵占为主,以生活腐化为辅,这种腐败具有直接性、暴力性,往往表现为对下层人、财、物赤裸裸的强抢和血淋淋的豪夺。
形象地说,这是一种占山为王的强盗式腐败类型,无异于杀人越货、火中取栗。西方学者对“中华帝国”的研究结果显示:“尽管对社会随时间变化而分化不能进行准确的数量度量,但中国一直是一个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。在社会的顶层,是一个富裕的阶层,他们只占人口总数的2%,却占收入的24%,处于社会底层的人,没有或只有少得可怜的土地,或许占大多数村子的家庭的20%至25%。”顶层和底层的分化,是封建专制滥权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。
笔者认为,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关键区别在于两点:一是政治上看是否出现了“法治国家、政党政治和选举民主”协同并立的政治体制和运作机制,二是经济上是否出现了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、产权制度和公司化治理结构。权力垄断集中和高度专制的政治体制下,传统腐败的极化、泛化现象十分突出。
用今天的观点来看,山寨式腐败的最大特点在于:权力无边界,责任无底线,利益无保障。
——官员们俸禄微薄,用官位自肥,但终难逃皇帝抄家;
——权力无边的皇帝可以明抢百姓家产,抄大臣的家;
——最后,流民起义,也可以抄皇帝的家!
在这些贪渎庸碌的大明皇帝统治之下,中央和地方政府出现了严重的“苏丹化”倾向。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“二十四史”,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、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。其中《明史》是毛泽东圈点最多、体悟至深的史书之一。
1964年5月,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:“《明史》我看了最生气。明朝除了明太祖(朱元璋)、明成祖(朱棣)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,明武宗、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,其余的都不好,尽做坏事。”
万历皇帝就是这“坏事做尽”的“苏丹化君王”的典型,在他的“断头统治”之下,大明朝廷犹如一个强盗云集的山寨,不论长幼尊卑,无不以强抢明夺为能事。
2.皇权勾连资本,天理遭逢人欲
问题在于,由史上出身最卑贱的皇帝开国并一度采取“剥皮实草”的酷刑治理贪官的大明王朝,怎么就变成了让毛泽东“最生气”的腐朽乱世?
读明史,发现两个今人耳熟能详的常见词:一是商人;二是资本。而且,“自神宗以来,黩货之风日甚一日,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,数十年于此矣”。明中后期,“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”。除了食君之禄的职业之外,大家都在忙着做买卖逐利赚钱,这是数千年未有之现象。在商人、资本、官商等关键词之间,给出了一些透析中晚明沧桑巨变的比较重要的线索。
如徐芳《三民论》曰:“夫商,携货而出、操母以致子也。”这是一个绝妙的譬喻,说商人们所经营的货币如同是母体,商人的本业就是让“银子下崽”。这道出了农业文明主宰的明王朝中,另一个将在19世纪的美利坚成为主宰的新生事物在初试啼声。它就是:资本。至于商人“操母致子”,无非是体现出了资本增值功能。但政府需要“先使未来钱”,而商人渴望“让银子下崽”,这使得官员和商贾之间有了一种源于资财的合作前提。至于后世资本家与政治家的联手,就是其高级形态而已。
再如《明实录》(正统五年一月丁卯)载:“给还盐商资本钞。时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奏:各处纳米中盐客商,有永乐中候支,到今祖父子孙相代,尚不能得者,艰难百状。乞如洪武中例,给钞还其资本以便民。”这段史实表明商人从一开始就要和官府打交道、找生意,如果官府作梗,商人只能是“艰难百状”。因此,所谓的“官商勾结”恐怕并非都是商人的一厢情愿,而很大程度上是在权力经济形态下的无奈之举。
因此,当大明帝国在时光长廊中邂逅资本的时候,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:
其一,是名教无存,“天理”让位于“人欲”,穷奢极欲取代儒家道统而占据了人们的脑袋;
其二,是资本张目,“商人”勾连上“官人”,金钱利益置换道德文章而充斥着权贵的口袋。
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被梁启超称为“政治地理学”佳作,其中记载了万历朝时世“迥异”之状:“富者百人而一,贫者十人而九,贫者不能敌富,少者反可以制多。金令司天,钱神卓地,贪婪罔极,骨肉相残。”对于金钱财富的威力,这番描述堪称入木三分。当时的一首民歌唱道:“世间人睁眼观见,论英雄钱是好汉,有了他诸般称意,没了他寸步也难。拐子有钱,走歪步合款;哑巴有钱,打手势好看。”
万历十六年(1588年),文人薛论道写了一组散曲《题钱》,其中有云:“人为你名亏行损,人为你断义辜恩,人为你失孝廉,人为你忘忠信。细思量多少不仁,铜臭明知是祸根,一个个将他务本。”为了金钱就可以完全不讲道德,利欲观念膨胀,背信弃义,胡作非为,整个社会疯狂到了极点。
明末人赵南星在其《笑赞》中讲了一个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,说的是唐三藏到了雷音寺,迦叶长者索要小费,三藏只好将紫金钵给他。愤愤不平的猪八戒到释迦牟尼那里告了一状,没料到结果竟然是:
佛说:“佛家子弟也要穿衣吃饭,向时舍卫国长者请诸弟子下山,将此经诵了一遍,讨得了三斗三升麦粒黄金,你那钵盂算有多少金子?也在话下!”说得个猪八戒好似箭穿了雁嘴,恼恨恨地走出来说道:“逐日家要见活佛,原来也是要钱的”。
这个故事分明是托事讽今,用天国的拜金来暗喻尘世的龌龊。金钱成了社会权力重新分配的一般等价物,也成了宗法等级制度逐步消解的强烈腐蚀剂。
然而,这“天国”与“人世”、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之争确是众说纷纭。如明末清初学者陈确就曾直言:“人欲不必过为遏绝,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”,“学者只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,则人欲即天理矣,不必将天理、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。”然而,实际操作中,从欲随心与枉法肆行难以区隔,纵情任性与贪渎滥权几乎不分。
陈确还代表时人心声痛切指出,士大夫“以治生为本”“治生尤切于读书”,“故不能读书、不能治生者,必不可谓之学;而但能读书、但能治生者,亦必不可谓之学。唯真志于学者,则必能读书、必能治生。天下岂有白丁圣贤、败子圣贤哉?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、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,与18-19世纪资本家在英、美两国的境遇不同,资本的芽苗虽然在彼时大明的朝堂上和草野间疯长,但却始终未能如“第三等级”和“强盗大亨”那样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。
首先,如马克思曾在《资本论》中指出的:“在中国……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,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。”关于明人笔记小说《松窗梦语》中一些家庭手工业发展成资本主义作坊的论述,以及苏州等地所出现的“机户出资,机工出力”现象,虽然透露出早期资本家(机户)和雇佣工人(机工)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,但却始终是“星星之火,未能燎原”,没有突破农业社会的枷锁而健步走上工业革命、金融革命的道路。
其次,由于权力经济形态下的商人从未获得独立的政治社会地位,从骨子里仍然难舍“由富而贵”的渴望。如李约瑟和黄仁宇所说:“官僚思想对成功的商人家庭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,一如催眠一般。”“官僚制国家有它自己的推动力。如果对社会稳定的渴求超过了经济增长或普遍繁荣,我们不妨说,维持一个基本的农业社会结构,比从事甚至允许任何形式的商业或工业发展,更有利于朝廷和官僚士大夫”,这也是“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”的政治原因。
因此,17世纪的明朝腐败高发期中,权力经济和商业经济的交错,商人阶层和权势阶层的博弈,犹如矗立在众匪云集的山寨周围的栅栏,包围着掠夺者打家劫舍的势力范围,同时也护卫着传统腐败的运作空间。
(本文节选自《走出腐败高发期——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》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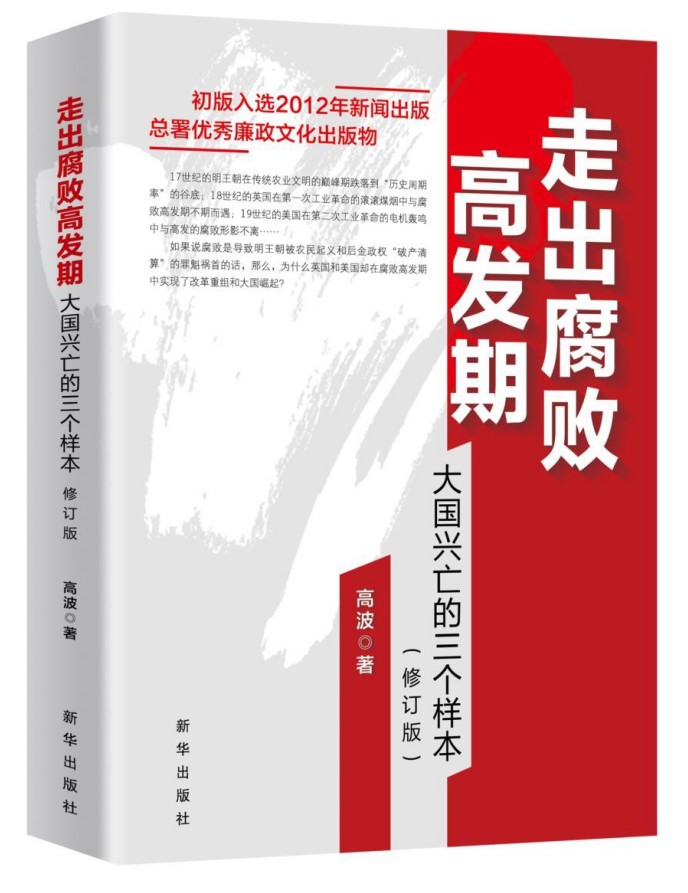
《走出腐败高发期——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》
ISBN:978-7-5166-5411-8
高波 著
新华出版社 2021年1月
定价:98.00元
